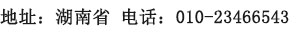疫情下,很多孩子不能及时开学,上网课成了大家一致的选择。
一般孩子在家上网课都是这个状态:
还有在线上体育课的,心疼老师一分钟。
在线的学生往往是这个样子的,老师看到的是“群娃乱舞”。
还有的老师累成狗,学生却悠然躺在被窝里的。
年轻的女老师可能会为了直播课早早起床,洗头化妆;年长的老师可能会为了一个在线签到而研究一天;体育老师为了呈现完整的动作,可能线下录制好几遍……
而面对着冰冷的电脑屏幕,原本面对面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问题,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再加上批改作业和答疑时间,老师们几乎成为了24小时的在线客服。
然而,对于有的学生来说,上网课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很多贫困地区,信号还覆盖不到,孩子们只能翻山越岭的找信号,去学习,去上课。
他们不能像上面的那些孩子一样,幸福的在家里,无忧无虑的上网课。
在西藏昌都,有一位在雪山山顶上学习的姑娘,她叫斯朗巴珍。
在毫无遮蔽的风雪中,坐在石头上学习,一学就是四个小时。
因为要写字,她连手套也不能戴。
为什么要在这里学习呢?
因为斯朗巴珍家的四周都是雪山,没有信号,只有在这雪山的山顶上,才有信号。
为了学习,她只能从2月19号学校开网课开始,就每天花30分钟爬到雪山顶上,在寒风中学习。
好在西藏昌都市移动公司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致电学校,询问了斯朗巴珍的家庭住址及联系方式。
在2月25号开始进行4G基站搭建,2月29号基站搭建成功,信号满格!
斯朗巴珍终于可以在家上网课,好好学习了!
在陕西省镇安县的青铜关镇,有一个老阳山村,
有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挤在简陋的帐篷里,或蹲或坐,
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捧着书本,
认真的盯着屏幕里老师的讲课,
小手在快速的做课堂笔记。
搭帐篷的这个地方,在离他们村子5公里外的箭封垭山顶,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手机才有信号,孩子们只能每天徒步5公里上山,
山上的气温已在-10℃以下,一顶薄薄的帐篷,又怎能给他们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呢?
从学校把延迟开学改成上网课起,河南南阳淅川的高三学生小通,每天早上8点都会准时的搬着小板凳,带上一天的学习资料,冒着寒风在邻居家的屋顶开启一天的网课学习。
因为家里没装宽带,他只能向邻居求助借wifi,而屋顶的信号最好。为了不打扰邻居,他便将屋顶当作自己的教室。
上演了现代版的“凿壁借光”,他说,他的目标是考上浙大!
让我们为这位“屋顶男孩”默默祝福吧!
在云南会泽县的某个村里,每天早晨7点,都有3名高中生约好一起爬山。
他们不是去看风景,而是去3公里外的山顶找信号,上网课。
爬山毕竟和走平坦道路不同,路上要走半个小时。
早晨气温很凉,有时候还会下雪。
在他们所读的东陆高中,全校这样的学生有大概多个,
因为会泽县大多数学生都住在山区,网络问题导致他们不得不跋山涉水的找信号。
这只是当地一所高中的数据,其他高中恐怕也差不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屋顶老师”、“山顶女孩”、“屋顶男孩”……
他们的生活就是现代版的“凿壁借光”,因为教育基础设施缺陷,而付出了比同龄人多十倍的努力。
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疫情来了,当然要去上网课。
但我们没有想过,没有网络条件的孩子们,他们去哪里上网课?
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疫情来了,当然要用智能手机来学习。
但我们没有想过,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
根据年《中国数字乡村报告》的统计,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也仅为38.4%
还有很多地方,算在普及范围内的,信号也差到用不了4G,那么智能手机还不如老式的诺基亚好用。
目前能覆盖到绝大多数农村的,只有电视直播上课。虽然农村没有网,但电视大部分还是有的。
但电视直播,每天各年级学生顶多能上一节课,知识量还是达不到。
所以普及网络,普及智能手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还任重而道远。
尽管我们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基建狂魔”,但是世间总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一步一步来,中国基建是老百姓的基建,不是修建了多少富丽堂皇的宫殿,而是在穷乡僻壤里修建了跨越鸿沟的隧道大桥!
中国基建之所以牛,就是在别人都摇头放弃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的从0做到!
若不是疫情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些被隔绝在山里的孩子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稳定的网络。
但我们也不可操之过急,路总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国每一个穷山沟里的孩子都可以上网课?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未来一定可以实现,时间不会太短,过程也不轻松,会有基建人的汗水铸就!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