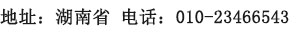看到你们格外亲
年9月20日死人沟
军车长龙,那是天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高大威猛,撼天动地,气贯长虹,整齐划一,绵延不绝……即便用尽所有的文采,也难表其一。
在国道,在国道,在戈壁,在雪山,我们或与军车长龙擦肩而过,或与军车长龙形影相随。几次,我把车停在路边,仔细打量着这支神奇的队伍:逶迤的铁甲、奇特的装备、隆隆的吼声,把我这个曾经戎马十年的老兵搞得热血沸腾、豪情万丈,仿佛年轻了三十岁,仿佛又回到了点兵的沙场。
抬起右臂,五指直伸,掌心向下,指尖触眉:一个庄严的军礼,一个老兵的军礼。战友们,你们辛苦了!
一声战友你会懂。
当年,边疆烽火又起,随部移防塞北半截塔(塔身风蚀一半得名),那山、那雪、那塔如在眼前。
车马走西沙走东,形如阵雁气如虹。
三山雨雪三山断,半塔风云半塔空。
野哭声声催戍角,梦回处处枕长弓。
王师一夜扶摇上,四海千秋在眼中。
如果说,平原地区的军人可以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来形容的话,那么在雪域高原,最恰当、最贴切、最有特点的形容军人的话应该是:缺氧气不缺士气,海拔高斗志更高!何等气势!曾经几次,我在青藏高原的山坡、在军营四周的围墙上看到这句惊天地、泣鬼神的标语,都不由自主地为它呐喊,为它高歌。
这句话是高原军人训练生活的真实写照。
高原的军人有高原的个性:驻守在屋脊上的屋脊,行走在禁区中的禁区,战斗在死亡中心的死亡中心;越是不可能越要可能,越是没有办法越要想办法;多少年来,他们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挑战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极限。
天路上那一道亮丽的色彩,就是用无数军人的鲜血和生命染就的。
毋庸置疑,西藏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西藏的历史却是一部辛酸的历史,多数时期游走在中华的边缘,与中原华夏若即若离。历朝历代或是“和亲”,或是由其“称臣纳贡”在形式上保持对西藏的主权。清政府曾派出驻藏大臣,到了袁世凯、北洋以及蒋宋王朝,中央都不曾在西藏驻扎一兵一卒。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驻军的主权是软弱的主权,没有驻军的西藏是苦涩的西藏。每每边疆有事,中央政府总是鞭长莫及,顶多不过敕命几句;如是,西藏成了待宰的羔羊,外族觊觎频繁,边疆蚕食不断,暴恐“独立”之声时不时响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和平解放议成,中央一声令下,解放军第十八军自昌都、青海、新疆、云南四路并进,把五星插上了喜马拉雅。
自此,雪域高原有了第一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
西藏千百年来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新中国伊始即成为不可分割的铁的事实。看得出,这并非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敢不敢的问题,它拷问的是国家的决心、政府的实力以及军人的忠诚。
当然,山高路险,征途漫漫,进入西藏的艰难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高寒缺氧,物资匮乏,扎根西藏更是艰难;民族、宗教错综复杂,动辄牵动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驻藏部队要得到藏族民众的认可、拥护甚至爱戴,岂止难上加难。
国道在藏北无人区有一个必经之地——死人沟,闻之不寒而栗,走进又寒又栗。由于名字太过惊悚,现已改名泉水沟。几十年了,泉水沟寂寂无闻,而死人沟英灵不散,被千万次地念叨。
死人沟海拔多米,四周的山铁幕一般把外面的世界挡得水泄不通,把一条“沟”似的山谷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于是,本就稀薄的氧气更是稀少。传说,曾有一支兵马在此宿营,一夜间全部死于非命。从此,“死人沟”这个惊悚的名称便不胫而走、不翼而飞。
即使现在,每年五月开山,沟里总能见到抛锚的汽车,车上人员坐姿如初,但已没有了生命,稍一触碰便赫然倒塌、破碎,连死亡的时间也难以确认。驻新藏线的武警部队,8年来共救助遇险的游客多人次。
就是在这种环境,人民解放军扎下了根。
解放军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戴有很多理由,我以为重要的是坚持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更重要的是坚持了“生产与修路并重”,战时是军人,平时是筑路工,在他们脚下,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公路一一通车。如今,青藏铁路也通了,川藏高速正在高歌猛进……
正是如此,我们川藏、新藏之行才一片坦途。
人们说,高原的道路是用鲜血和生命砌成的,这话并非夸张,仅国道的养护,就把多条生命埋葬在了高原。子弟兵把天堑变成了天路。有了天路,输向高原的物资源源不断;有了天路,藏汉已然一体;有了天路,中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大动脉全部贯通。
车过死人沟,九口一声呼叫:右前方,一色军绿大卡排着长龙,正向高山挺进。我一脚油门赶上,军车礼貌地让出左道,我们行驶在一列长长的军车左侧,像极了阅兵式。九口打开车窗,一手对着军车视频,一手伸出大拇指为雪域高原的兵哥哥点赞!
说来也巧,我们在路边的餐馆午餐,赶上来的军车也停了下来。官兵陆续下车,军容整洁,高原的阳光让他们的脸庞红里泛黑,更加增添了英武帅气,仔细看,一色年轻的小伙子,眉宇间不无稚嫩。他们到餐馆三三两两坐下,有的点了面条,有的只坐着看手机。
我很是奇怪,以我在部队生活的经验推测,部队应有后勤专门负责伙食,统一安排,哪有单兵作战的?问旁边一名士官:“部队不安排午餐吗?”
士官羞涩地笑了笑,黝黑的脸露出一口洁白的牙,说:“午餐在兵站呢,这里到兵站还很远,扛不住,垫巴点。”
懂了,不是进餐的点,也不是吃饭的地儿,饿了,自己开个“小灶”。
生龙活虎的后生,正是成长的时候,与千万家庭的孩子没什么不同,本是家长精心呵护的掌上明珠,在父母跟前,都是饭来张口的宝贝疙瘩,即便搞个东餐西餐也是小意思,而在远离父母的高原,在顶不住的时候,只能一碗面条,还自掏腰包。我们吃得虽不豪华,也两菜一汤,面对几下就把面条倒进肚子里的子弟兵,满是尴尬。
后来,九口对我说,当时咋就没有点几个菜招呼他们一起吃呢?
是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居然没有想到。懊恼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抽自己。这事成了我们心中许久的痛,每每想起都悔恨不已,直到现在。
匆匆忙忙,车队又出发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内心仿佛有一种声音:请接受一个老兵诚挚的歉意,但愿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