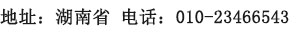无论是我们祖辈、父辈所经历的集体时代的“露天电影”(“坝坝电影”),还是现在我们坐在繁华的都市影院中观赏的“现代电影”,看电影已经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惯习化”,我们不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电影?是被电影文本吸引?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进而,我们更不会去追问我们是怎么看电影的?又为什么能够看到这部电影?这事实上涉及的是与电影相关生产、放映与制度等问题。云南大学郭jianbin教授在其新书《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中,就向我们回答了上述问题。
作为一部“民族志取向”(注1)的传播研究著作,这本书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自年以来,以位于中国西南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为田野地点(注2),以流动电影及其相关的“媒介实践”(注3)为考察对象,在较为扎实而深入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由作者独立完成的一本学术专著(郭,:前言1)。在书中,作者围绕“在场”这个分析概念,从国家“在场”、“转场”和观影者“在场”三个面向串联起了流动电影实践的三个维度:生产(注4)、放映和观看。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书中的三个关键性概念“在场”、“转场”和“守望”之中。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这本书,需要从这三个概念讲起。
一“在场”
如前所述,全书的结构层次是在“在场”这个核心概念之下铺陈开来的。关于什么是“在场”,作者在“导论”部分首先就进行了界定:“所谓‘在场’,指的是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郭,:2)进而作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
笔者认为,沿着作者的思路,“在场”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在场”是一个特定的“媒介时空”。这个时空是由特定的传播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媒介生产、消费等活动构成。就本书的讨论而言,就是指与流动电影相关的“媒介实践”。同时,媒介时空和社会时空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就区别而言,媒介时空较之于社会时空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媒介时空中“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也就是说,由于在媒介时空中,时间是可逆或可重复的,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场”和“不在场”可以同时呈现于其中。特别是那些“不在场”是如何通过媒介的连接而具有了“在场”的意义,更是应该成为探讨这一特定媒介时空中“媒介实践”的关键。而就联系而言,首先,媒介时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时空。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时间和空间的“成交”(emptyingout)使得社会诸关系的延伸成为可能(转引自杨雅、喻国明,)。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的交织共同构筑起社会力量的根源。因而媒介时空中同样存在着一个社会的维度,只不过这个社会的维度是经由媒介建构的。其次,媒介时空只是诸多社会时空中的一种类型,它既与其它社会时空交织在一起,又和其它社会时空相互组构而形成更大的社会体系(socialsystem)。这就意味着,媒介时空中必然含有社会时空的逻辑,用作者自己的表述,就是必然与一个“社会结构空间”(郭,:8)有关。
第二,“媒介时空”中的媒介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媒介实践”。如前所述,媒介时空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被置于更大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时空类似于布迪厄(Bourdieu)学术话语中的“场域”(field),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行动者、行动、互动、关系、位置、规则、结构、权力等要素。因此,在媒介时空中展开的流动电影,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电影文本有关的看——这也是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