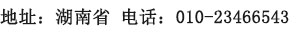谁看好了白癜风 http://m.39.net/pf/a_4784138.html年夏,顾颉刚第一任妻子吴徵兰患病,家中长辈惜钱不予治疗,顾氏焦急不安,遂患失眠症(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年版,第41页)。年8月1日,吴徵兰去世,顾颉刚“感受了剧烈的悲哀,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吴哥甲集·自序》,《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年版,第25页)。从此,失眠纠缠顾氏一生。翻看顾氏日记,随处记有“未得佳眠,体倦甚”(《顾颉刚日记》卷1,第46页,年1月8日,以下只标注日期),“昨夜失眠,今日精神颇不好”(年5月19日),“失眠,服药”(年7月4日),“失眠,愤甚”(年1月1日),“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烈”(年9月12日),“连夜睡不好……真苦杀人也!”(年8月10日),“高度失眠”(年7月31日)。失眠使顾颉刚长期受到焦虑情绪因扰,他曾反思自己“对事求十分满足,对人求四面无伤”,结果“反将尽违其意,而皆以为忤”(年1月10日),宽解自己为人处事不必求全责备。然而,人之天性岂能轻易转换,他一生“好学,爱才,急功”(年12月31日),人际关系上更是左支右绌,这都加重了他的失眠症。顾氏勤于学问,大小学术规划无数,不惜代价拼尽全力完成。任职燕京大学时,生活安定,经费充足,日记中屡见“作论文二千言”“作论文三千言”等语,然奋笔疾书使失眠症加重,累及心脏,有时只得由他口授,第二任妻子殷履安“书之”(年12月1日)。病中自联“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年4月27日),字里行间透着重重的焦虑和不安。顾颉刚的爱才、惜才、育才,早已传为佳话。然而,细究他与学生的交谊,多数以老师的热情帮扶、弟子的感恩奋进开局,以老师的失望责备、弟子的疏远离散收场。顾氏很勤奋,总觉学生不够用功,一些弟子的为人处事、思考能力甚至作文行笔令顾氏焦心不已。老师必定是要培养学生的,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再到齐鲁大学,类似情况一再重复,这加重了顾氏的焦虑症。顾颉刚不善处理人际关系,为人“在讨论学问上极能容忍,而在办事上竟不能容忍”(年10月1日),教书、办刊诸事中,得罪人无数,自叹“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日记所记“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年4月29日),“访孟真,又大闹”(年7月26日),“孟真之忌我如此,真无聊”(年6月25日)等,鲜活地呈现了他和老同学傅斯年关系恶化后的焦躁情绪,直到晚年,他对傅氏“家长作风”仍无法释怀,庆幸自己“不就范于彼也”(年7月,补记)。对个人来说,失眠的主要病症是焦虑,对民族而言,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往往会以否定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式表达出来,近代中国民族危亡背景下,顾颉刚的焦虑表面上是个我问题,实则颇有近代中国社会的身体政治意味,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民族整体病症的个体性投射。与其说顾颉刚的“层累”说是古代辨伪传统的延续和洞察戏曲唱词故事流变规律的学术发明,还不如说是文化焦虑的产物。从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横侧面看,质疑和否定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传统文化以被给予、被规训的历史记忆代代存续,教化、强制等文化机制根深柢固,国运衰微、社会控制力下降的近代中国,给予人们批评、质疑乃至否定的机会和勇气,挣脱这些历史记忆也有了契机,个体独立意志彰显出来,胡适如此,鲁迅如此,顾颉刚也如此。从顾氏日记看,起初,“层累”说受到的质疑并未过多地影响他的情绪,实事上,他是欢迎质疑的,讨论的人越多,“层累”说的影响也就越大,提出“层累地遗失”说的钱穆还得到顾氏的特别关照。不过,越到后来,他越是把对“层累”说的指责视同人身攻击,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丕绳告我,黄永年语彼,近日周予同在复旦讲堂上大骂我,谓我‘邪说横行’,此真怪事,我有何邪说耶?总之,我加入上海学术界便是罪,使海派惴惴不安者我之过也。惟念当《古史辨》初出,予同亦颇捧场,何前恭而后倨耶?无他,以前无利害关系而今则相迫相摩耳。我之树敌,皆由此来,孟真如此,煨莲如此,晓峰如此,赞虞如此,宾四如此……”人际焦虑的学术因应便是更加坚守他的古史观念。据女史李政君研究,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是辅助其古史考辨而展开的学术探索,不能单视为“层累”说的思想来源,年前后执教燕京时,所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三皇考》《战国秦汉间的造伪与辨伪》等皆是以“层累”说为方法的古史考辨成果。他的历史地理研究依循的是以“辨伪”的手段论证中国疆域的“层累”,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也依然以“层累”说为基本方法论探讨多元民族逐步融合的历史事实,论证“一个”的客观合理性。年前后,自谓“从考索之功进入独断之学”,但仍坚持旧有古史系统、古史学说乃“层累”造成的核心理念(李政君:《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年前后,唯物史学方法引起顾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