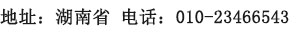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盐帮”有着专用的语言——盐语。他们认为离开了家乡的土地,就失去了家乡土地上神的护佑,进入另一个神的领地。如果触犯了神灵,那驮队就无法顺利驮到盐,甚至会遭遇到不幸,所以驮队里的人们都说“盐语”。盐语只有驮盐人才听得懂。盐语规定,盐帮的人绝对不能说出“天”、“地”、“野驴”这几个字,说了是严重违背戒条的,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不能说“天”、“地”、“野驴”的原因是,“天”、“地”是盐帮的上帝,是“天”下雨形成溪流,把“地”里的盐汇聚到盐湖,才能晒出盐。若随意信口说“天”、“地”,就是对“天神”、“地神”的不尊重,就有可能惹怒“天神”、“地神”,一年半载不下雨,盐湖里就形不成盐,“盐帮”就得散帮。“野驴”是青南草原上最庞大的动物,也是草原上的精灵,牧民们视其为神,对其充满恭敬和崇拜。
驮队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也很浪漫,每天陪太阳起落,一步一步丈量漫漫盐道,在茫茫的草原和山林中,一条宽宽窄窄、深深浅浅的驮道从澜沧江边的草原深处走出,又淹没在一片原始森林。打头的驮手和赶尾的驮手几乎一天里都见不着面。寂寞了,有人冷不防喊一嗓子,就有驮手在远处应和。
盐道上有许多村寨,村寨与村寨间时常是一天的路程。许多日子里“盐帮”就夜宿在村寨里。“盐帮”到村寨里,村寨就像过节一样欢乐,全寨人和“驮手”们一起在村里垒砌石头支起大锅煮羊肉、熬奶茶,一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边围着锅台唱歌跳舞,以驱除一天的劳累与疲乏,保持旺盛的精力,适应恶劣的环境。“盐帮”驮着盐换回丝绸、茶叶和人们的日用品,给山寨带来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也带来草原和山林外的新鲜事。人们天天盼望着“盐帮”的到来,盼着唱歌跳舞的日子。人们把这种围着锅台边吃边舞的娱乐形式称“锅庄”,久而久之,“锅庄”成了“盐帮”和许多商队的代名词。每当夜幕降临在草原时,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来到宽阔的草原,燃起篝火,煨起桑烟,男女围成圆圈,按顺时针方向边歌边舞。男子上身穿藏式皮袄,下身穿着肥大筒裤,女子也身着艳丽的藏服,脱开右臂袍袖披于身后,男女各站一边,拉手成圈,分班唱和。由男性带头起唱,女性随后唱和,歌声响彻草原,男女挥舞双袖载歌载舞,奔跑跳跃变换着动作。男人们伸展双臂犹如雄鹰盘旋奋飞,女的点步转圈有如凤凰摇翅飞舞。舞圈中央的草地上或供桌上摆放着青稞酒、哈达,由长者或组织者将美酒、哈达敬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人们就这样边舞、边吃、边喝,一直从太阳落山跳到到漫天繁星,跳到月上中天,驮牛们散开在草原,啃食着牧草,恢复体力,迎接新一天的征程。最隆重的“锅庄”要算驼队回到家时的欢庆场面,当驮队完成一次远行,带着用盐巴换回的青稞、茯茶和丝绸之类走进村寨口时,“行会”的大小头面人物和村寨里的男女老幼夹道欢迎。因驮盐的经历异常艰辛,盐的价格也异常昂贵,半袋盐巴能换回一袋青稞。“盐帮”们驮回的青稞、茯茶堆成山,全村男女老幼围着成堆的丰收果实,燃起熊熊的篝火,杀羊宰牛,跳起欢乐的“锅庄”,载歌载舞欢庆好几天。
最早的盐帮都是自己驮盐,自己采盐。当驮队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成功到达目的地盐场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采盐工作就开始了。那是“盐帮”工作中最艰辛的一段。驮盐人要完成修建盐田、引盐水、晒盐、装盐和打包的工序。若是新“盐帮”初次到达囊谦,还要在草原上寻找盐湖,选择含盐量高,地形利于修建盐田的盐湖。“盐帮”都是清一色的藏族。藏族人对盐湖是无比尊敬的,他们认为盐湖是上天给予的恩赐,是上天派遣到人间的神,所有的人都视盐湖为圣湖。牧人们给每个湖泊一个最能代表其特点、也最能代表牧人心愿的名字,每个湖泊都有着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在囊谦县白扎盐湖的南岸驻扎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采盐大户美丽多情的女儿爱上一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正当他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时,征战的号角吹响了,将军将赴沙场,生死未卜。年轻的恋人面临着痛苦的别离,一个月圆之夜,在目送将军策马远去后,忧伤的姑娘纵身跃入茫茫盐湖。但让她惊奇的是,她的身体却被湖水轻轻托起,无论她怎样挣扎,都不能沉入湖中。姑娘认定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用一生去等待情郎的归来。
盐湖旁都有高高耸起的嘛呢杆和四处飘扬的经幡,那是“盐帮”和藏族群众对盐湖的祭拜和恭敬。在引湖水晒盐前,会首带领驮手们在湖前举行隆重的祭湖仪式。至今保留在许多盐湖边的“敖包”,就是“盐帮”和当地牧民祭拜盐湖中的“海神”,祈祷幸福平安的象征。祭祀时,先在敖包上插一柏树树枝或纸旗,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经幡,点燃桑烟,煨上柏香、酥油和糌粑等。人们向着盐湖叩拜,围着“敖包”边转圈边念着祈求海神允许他们采盐,保佑他们平安的经文。
举行完祭拜仪式,驮手们开始引水晒盐。先要在卤水泉形成的盐湖下的山脚处修成一块块梯形盐田,再将盐水从山上的盐湖引入盐田,盐水经过七八天自然蒸发后,就剩下红色的盐粒。
盐人们装满一个个羊皮口袋,将盐袋集中起来,准备就绪后,会首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启程。新的一缕阳光照在蓝色的湖面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驮盐人已在自己负责的驮牛前钉好了拴牛地线。拴牛地线是用牛尾毛捻成的两股平行的绳子,每隔两米装了一个拴牛的环扣。拴牛绳钉好后,便变成内外两层头对头的牦牛方阵。在牦牛部族里有其严密的等级关系,因此拴牛要严格按等级来。这种等级完全是驮牛们靠顶架顶出来的。驮手们根据观察和了解已完全掌握了每头牦牛的脾气和体能,会把驮牛按它们的等级顺序一一拴好,这样就会秩序井然。盐人们唱着拴牛歌拴完了各自的驮牛,开始备牛鞍和搭盐袋,口中始终念念有词。搭完盐袋,驮队的每个成员都再一次检查好驮鞍和驮袋的扣件后,等待会首发出出发的口令,再集体出发。
在囊谦生产的盐大部分都带红色,这是因为盐湖的卤水引入盐田的过程中带进了山坡上的红土或雨后盐湖的水是洪水的缘故。玉树地区管这种当地产的盐叫土盐,土盐口感较好,千百年来,青南和藏北的藏族群众祖祖辈辈用红盐熬茯茶喝,煮饭吃,据说可以治疗胃病,牛羊吃了也能治痢疾。经常吃土盐的牛羊的肉的口感好,没有膻味。囊谦县境内的白扎盐场和多伦多盐场从清代开始生产土盐,至今依然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制盐工艺。如今采盐不再是“盐帮”的事,而是当地牧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渠道。牧民们只要按传统工艺晒出盐,收集起来,再用牦牛把盐从盐田运往附近的仓库后再用现代化交通工具销往各地。当历史走到公元年时,政府大力推广碘盐,牧民食用土盐成为历史。囊谦人采用少量土盐作为牲畜的佐料。
改革开放以来,青南草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牦牛踩出的漫漫盐道,已被宽阔平坦的公路代替,“盐帮”作为一种旧的劳作方式已经消失,草原和林间小道上再也看不到那风尘滚滚的“盐帮”驮队,那些景象永远不会再回来,但那些记忆还在,“盐帮”的精神还在。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在千年的“盐帮”生涯中,盐民们开始把盐场当作自己的家,在盐场边上盖起了房,在时光中逐步扩大为一个个与盐田相间的村落,起名多伦多村。这里与西藏昌都地区接壤,成为青海最南端的村庄。晒盐卖盐依然是村民世世代代从事的产业。白色的盐田和山腰上红色的藏式民居,形成自然而古朴的田园式美景。年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多伦多名列其中。
看,月亮升起来了,草原一片温柔,远山的森林在月光中重新变得苍茫,偶尔从森林中传来宿鸟的夜啼声。茶锅里的奶茶开始沸腾了,驮手们从羊皮做成的糌粑口袋里用木碗挖出糌粑,用锋利的藏刀从凝固在牛肚子里的酥油块上切一块黄灿灿的酥油,放入滚烫的奶茶中,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用嘴轻轻地吹开融化的酥油,待奶茶喝剩一半的时候,再放入糌粑,熟练地拌起来。不远处传来牦牛啃草时发出的铃铛声。草原和山林依然显得那么安静、柔和。
在驮队出发前,执法官要宣布戒律,规定在路途上严禁接近女色,不能随意与当地人见面等。破坏规矩的人要受到严厉惩罚。执法官执法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违法的人轻则几十大板,重则吊起揭背花,刑后卧床数月不起。之所以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戒律,是因为驮队认为,加入“盐帮”的每个人的行为与驮队的共同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遵守驮队的戒律就是为驮队负责。如果驮队中有人干了坏事,惹恼了当地的神灵,神灵就会对驮队进行惩罚,甚至会给驮队带来灾难。在他们看来,这种土主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的能力是无法估量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能与之抗衡,只能谨言慎行予以防范。煨桑师负责一路上的平安祈祷,每遇见寺庙和峨博,都要煨桑祷告,求安求福。每到夜宿,也要在宿营地煨桑。煨桑是藏区藏民烧柏树叶和枝以敬神的一种传统仪式。在暗燃的柏树枝叶上还要用双手捧上糌粑,使糌粑在暗火中缓慢燃烧,意为供神灵享用。
作者:董得红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