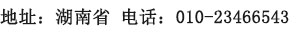文∣白猿
图∣唐旭本人提供
20多年前,不到20岁的唐旭来成都闯荡,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藏传佛教文化,从唐卡开始,走向了藏地和西行之路。之后的十多年,他多次往返印度、尼泊尔,特别是尼泊尔,很像现在的选品师,去选各种手绘唐卡回来,顺便帮朋友们带一些铜制佛像。
尼泊尔手工佛像代表着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佛教造像工艺,长期引领各个地区佛造像风格的衍变和技术上的革新,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他去到尼泊尔制作铜像的大小工厂和家庭作坊,看当地工匠的制作过程和生活状态,了解到佛像制作在尼泊尔的产业链和中国对佛像的大量需求。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去做好的手工铜佛像?”
也是从这个发问开始,唐旭走上了一条原创手工艺产品路:“做我们自己的铜佛像”。
十年做佛像
开始想的简单,我们国家可以做出那么多高科技的产品,做佛像肯定也没问题。他们从成都出发,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只要有铜器工艺的,都去参观,从北方找到南方,再回到成都,没有一家能做好的藏传佛教铜像。他们还曾经找到深圳一家工厂,出了条产品生产线,之后发现,买回来的机器完全用不上,前前后后浪费了两年时间,干脆自己做工厂、自己找师傅、研发技术吧。
工厂在成都郫县,做铜器的前两三年,唐旭一直守在工厂,请不同地方的工匠,包括尼泊尔的工匠来给工人做指导和培训,反复失败和总结,至少做了几千个样品,一直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工艺。
最初的难度来自工艺,中国传统的失蜡熔模铸造法最早起源于春秋时代,汉地有好的手艺匠人,但是藏传佛教的佛像和其他工艺品不同,每一尊佛像,包括身高大小,眼睛、鼻子、耳朵的尺寸,手上的法器、头冠衣饰都记录在《造像度量经》里,如果没有深入接触过藏文化,熟读佛经,很难做出藏地佛像的精神和韵味。一尊佛像做得好不好,泥塑非常关键,唐旭请到西藏日喀则的传统匠人,每年年底来成都一段时间,专做泥塑塑形,因为藏传佛教的铜像有一截是空心,所以铸造难度大。之后,包浆、烧制、浇铸、冷却成型,然后由汉地的匠人负责雕刻,处理纹路细节、精细打磨,泥塑可能会很快,后期的工艺需要花很长时间,最后彩绘、开脸,黄金磨粉,用毛笔尖一点点、一层层画很多层,为佛像开脸。
他做的是小佛像,最大的只有五十公分,小佛像的细节特别多,不同的工序需要不同的匠人,唐旭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汉族、藏族找,屡次试验和匹配,如果不合适,就自己培养手艺人,从塑形到细节,几乎是按照艺术品的标准来打造,细节到小铜像的手指都是分开的,佛的眼睛、眼神、手型都非常正统,他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人们会有疑问:“一个汉族小伙子,能把我们藏传佛教的佛像做好吗?”唐旭做到第四年、第五年,技术已经能达到尼泊尔的中高档水平了,之后最大的难度来自于市场的接受和认可:“从产品做出来到推向市场,其实是个很心酸的过程。“唐旭坦言,很多人看到这个佛像,说做得非常好啊,是尼泊尔、印度吗?如果没有否认,他就说这个太好了,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做的,他就会天然排斥:不会吧?肯定没有人家的好。
当然也有历史原因,国内最初那些年,在铜像制作方面大批量粗加工滥制作,造成了不良的市场影响,如今,原创品牌想要走自己的路,做精细化的佛像,一点点树立信心,其实特别困难。加之年轻人对传统手艺的淡漠,工匠的流失,和去年全球疫情的影响,这个行当愈发艰难。
十年,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漫长,但对他来说,太短了。古代流传下来常见的佛像种类有两千多种,每一个教派、每一种传承,包括每一个寺庙都有它自己的护法。唐旭现在做佛像只做三个尺寸,他算了算,这三种全部做完要做六千种,“我这一代人,包括我女儿这一代,都做不完的。”
“一步一步走来,这是我们坚持的第十个年头了,想做自己的佛像并且被大众认可,很慢、很难,需要时间去沉淀。”
三年拍贡嘎
做工厂,做中国原创佛像品牌的这些年,唐旭的压力特别大,内心也有非常多的矛盾时刻。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去藏区的路上,绕道去到康定机场后面的那座山,几乎在那里坐了一天,手机没有信号,没有打扰,就在那里看雄伟的贡嘎雪山,“一种享受”,他说。
“这也是我第一次拿起数码相机拍贡嘎,也是我拍这座山的第一个点位。”
与工作有关,其实这些年他经常进藏,去过藏区很多地方,这次是个偶然,他作为摄影爱好者,开始拍贡嘎,一拍又是三年,只拍贡嘎。“我们的蜀山之王,虽然海拔不是最高,但是山体雄壮,高度达到六千多米,东西南北面,完全是几种天地,可拍的点位和机位特别多。”
贡嘎一年四季都不同,相同的地方不同时间去也不同,拍贡嘎不容易,很多地方不通公路,许多垭口当地人都不会去,他只好多次找寻当地人多次确认点位,辛苦去到又要等,可能一天只出来几十秒钟,有可能等几天都不出来。
最初拍贡嘎,因为不熟悉闹过笑话,在牛背山的一个点位拍了三天,每天都有日照金山,回来后才发现,拍成了田海子山。这三年随着他的深入了解,查资料找当地人寻找点位,他发现了不少隐秘之地,比如他在一个山头上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非常壮观的黑石城,也从最初的十多个点位到后来越拍越多,现在已经爬了五十多个山头了,
有一个地方他去的最多,现在已经成为圈内网红之地:冷嘎措。他前后去了二十多次,有一半时间没有拍到,同样的季节第一天和第二天去都不一样。“有时候有风就没有倒影,没有风又没有蓝天,每次都没办法完美,人就是这样,越没有拍到好的地方,越想去,我听过一个冷嘎措的传说,有时我会想:冷嘎措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呢,喜欢我,为什么没有拍到好的照片,不喜欢,为什么每次又让我来。”
很多拍山的职业摄影师,都没有唐旭这么执着,他说自己只是摄影爱好者、贡嘎爱好者,用这种方式拍山,让他觉得减压。他把一次一次拍贡嘎当成自己和外部世界对抗和解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方式,也促成了他的不断深入创作。贡嘎沿线的人文、风土、信仰都不尽相同,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动植物和环境也不一样,一次一次深入,他想要了解和拍摄的题材越来越多。
“拍贡嘎,慢慢成习惯了,甚至做梦都会梦到它,有时我觉得好几天没拍了,就想去一下。”
两条没有捷径的路
有人问他,贡嘎的哪个角度是你最喜欢的,他说只要是我拍过的角度,去过的地方,我都喜欢。和佛像一样,不管是哪一尊佛,愤怒的、激进的、平静的、欢喜的,只要是真实的,我都喜欢。
之前,唐旭的展厅在成都武侯祠附近,藏族人聚集的地方,去年他在西边做了一个新空间:利美旭方,特地把展厅放在了离开藏族文化圈的地方,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在这里,做这个店的意义在哪里,生存空间在哪里,唐旭说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不了解藏传佛教文化的人走进来,接触到佛像和藏族文化,有机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空间的外墙有幅唐旭拍的巨幅横版贡嘎雪山的照片,走进展厅,也有一幅雪山图,这是他去年在山上待了七天七夜拍到的照片。去年五月份,唐旭带着助手上山,第一天乌云笼罩,他们在藏族老乡的棚子里搭帐篷,烤火、煮饭,第二天早上起来,大雪白茫茫一片,天亮了十多分钟,他们跑上山再下来的时候,雪大到连车子都看不到了。“雪太厚,很多牛羊都死了,我们前面有很多狼,雪太大,狼都跑不快。”没办法,待了三天,还是如此,一待就待了七天。
第七天,天蓝了,贡嘎出来,他们找了好几个山头和角度,最后爬到一个山头上,都快日落了。“那天的日照金山特别长,有多公里,我拍下来了,拍的时候全神贯注,拍完才发现,其他人都冷到不行了。”
“我就是要等,等到它出来,这是一种特别的人生体验。”拍贡嘎,唐旭是执着的,做佛像,他也同样如此,“开始做这个行业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如今我四十多岁了,已经坚持了这么久,走了这么长的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延续下去,不想辜负自己。”
如今,唐旭的铜器在西藏昌都、青海西宁、玉树等地都有店铺销售,他的贡嘎拍摄之路,也在持续进行中,“我计划去个点位,做一个环线拍贡嘎,东边、西边的点位比较多,很多我都去过了,北边的线路我也已经查好了。”
他选了两条看上去很笨的路,哪条路都不好走,没有捷径可循,不过他一直在坚持走,从未想过放弃。